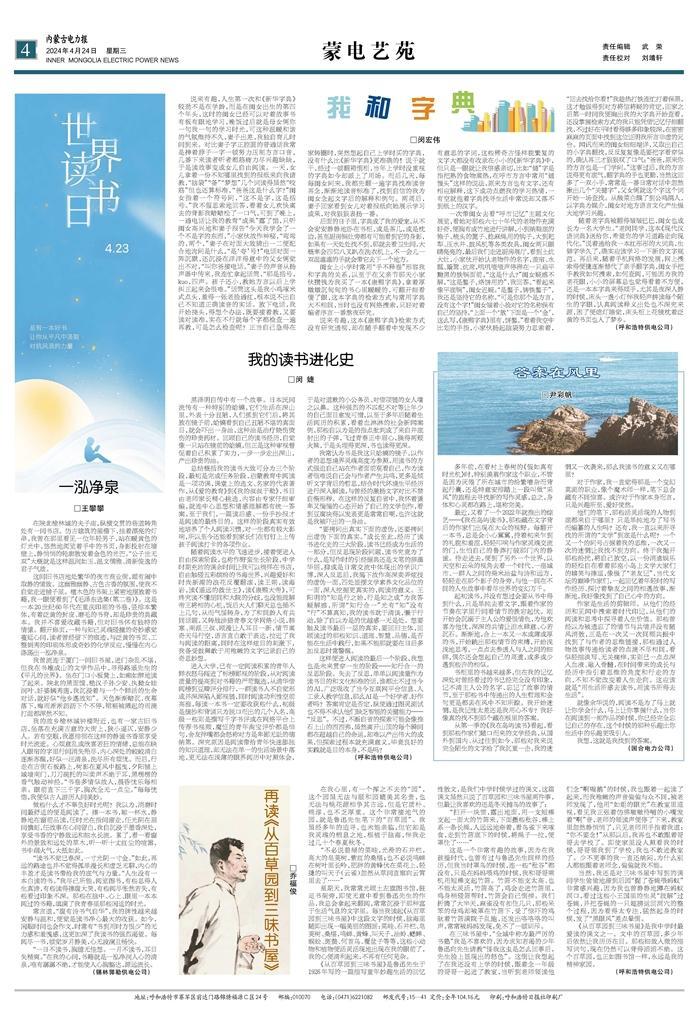
|
|
|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第04版:蒙电艺苑
第04版:蒙电艺苑
-
我和字典
说来有趣,人生第一次和《新华字典》较劲不是在学龄,而是在闺女出生的第四个年头,这时的闺女已经可以对着故事书有板有眼地学习,晚饭过后就是母女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学习时光,可这种温暖和谐的气氛维持不久,妻子出差,我独自育儿时间到来。对比妻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常是抻着脖子一字一顿努力压制方言口音,几番下来读者听者都筋疲力尽兴趣缺缺,于是读故事变成女儿自由阅读。一天,女儿拿着一份不知哪里找到的报纸来向我请教,“脑袋”“备”“梦想”几个词读得虽然“咬筋”但也还算标准,“爸爸这是什么字?”闺女指着一个符号问,“这不是字,这是括号。”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看着女儿欢快离去的背影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可到了晚上,一通电话让我的教育“成果”露了馅,只听闺女高兴地和妻子报告“今天我学会了一个不是字的东西,”小家伙故作神秘,“弯弯的,两个,”妻子在对面大致猜出一二便配合地询问是什么,“是‘夸’号!”电话对面一阵沉默,还沉浸在洋洋得意中的父女俩觉出不对,“叫你爸接电话。”妻子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来,我连忙拿起话筒,“那是括号,kuo,四声。孩子还小,教她方言以后上学纠正起来会很难。”话筒这头是我小鸡啄米式点头,羞得一张老脸通红,根本说不出自己不知道正确读音的实话。放下电话,我开始挠头,得想个办法,既要接着教,又要读对读准,实在不行就每个字都检查一遍再教,可是怎么检查呢?正当自己急得在家转圈时,突然想起自己上学时买的字典,没有什么比《新华字典》更准确的!说干就干,经过一顿翻箱倒柜,当年上学时没重视的字典如今却派上了用场。而后几天,每每闺女问来,我都先翻一遍字典找准读音再念,渐渐地读音标准了,找到自信的我为闺女念起文字后的解释和例句。两周后,妻子回家看到女儿对着报纸向她展示学习成果,对我狠狠表扬一番。
-
我的读书进化史
黑泽明自传中有一个故事。日本民间流传有一种特别的蛤蟆,它们生活在深山里,外表十分丑陋,人们抓到它们后,将其放在镜子前,蛤蟆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真面目,就会吓出一身油,这种油是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回顾自己的读书经历,自觉像一只站在镜前的蛤蟆,但正是这种审视督促着自己积累了实力,一步一步走出深山,产出珍贵的油。
-
答案在风里
多年前,在看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时,特别羡慕作家这个职业,不管是因为厌倦了所在城市的纷繁嘈杂而背起行囊,还是特意安排踏上一段叫做“采风”的旅程去寻找新的写作灵感,总之,身体和心灵都在路上,堪称完美。
最近,又看了一个2022年就推出的综艺——《我在岛屿读书》,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作家们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每翻开一本书,总是会小心翼翼,持着初来乍到的礼貌和羞涩,轻轻叩响与作家灵魂交流的门,生怕自己的鲁莽打破那门内的静谧。待走进去,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天空和云朵的视角去看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人之间的柴米油盐与诗和远方,轻轻走在那个影子的身旁,与他一同在不同的人生故事中看尽世界的变幻万千。
-
一泓净泉
在陕北榆林城的夫子庙,纵横交贯的巷道转角处有一间书店。仿古建筑的屋檐下,挂着漂亮的灯串,我曾在那里看见一位年轻男子,站在暖黄色的灯光中,悠然地浏览着手中的书页,身影投射在墙壁上,静悄悄的轮廓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公子世无双”大概就是这样温润如玉、温文儒雅、清新俊逸的君子气质。
-
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我心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园”,这个园虽无法与颐和园媲美其名贵,也无法与桃花源相争其古远,但是它质朴、绵淳,也不乏厚重。这个非常接地气的园,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我虽经多年的追寻,也未能亲临,但它却是我灵魂的栖息之地,根植于脑海,伴我走过几十个春夏秋冬。






